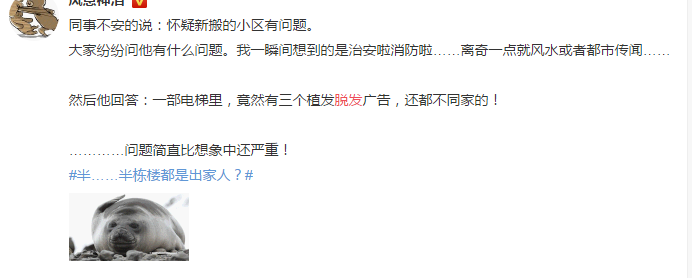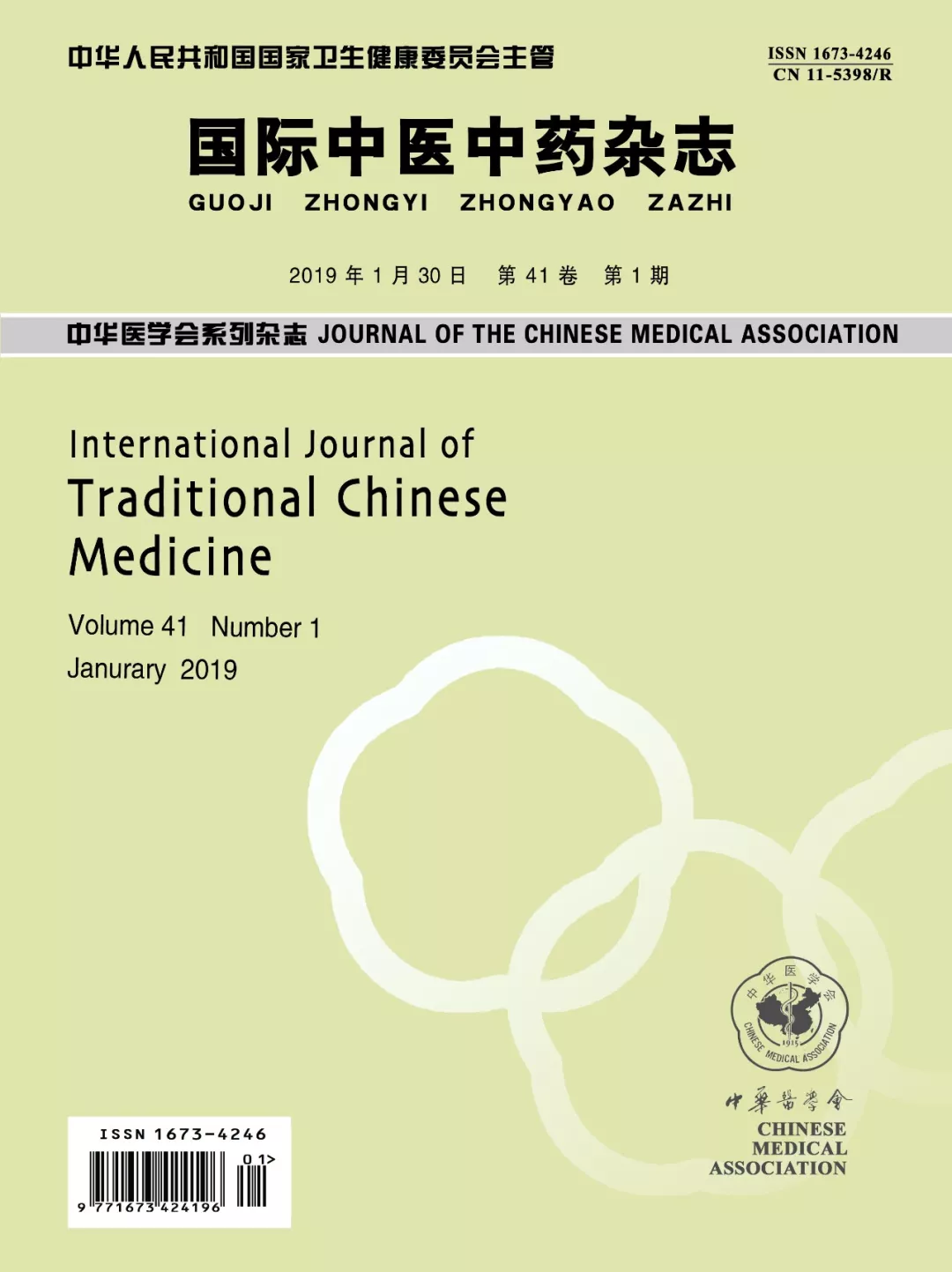一粒伟哥一碗馄饨
1.
2003年,我读大学一年级,经常收到短信,短信结尾署名:viagra。
我拿着手机去找舍友咪哥,问是啥子意思。
咪哥戴着比瓶底还厚的眼镜,俨然一渊博学霸,新生报到时,咪哥在床头抱着一本新华字典和英汉词典,啃得十分投入。送屁屁到学校的屁爸见了叹为观止,对屁屁说:你看看,人家外地的孩子就是专心。
咪哥不负众望,初露端倪时就锋芒毕露,令众人顶礼膜拜,佩服得五体投地。一次卧谈时,咪哥问了一个很深奥的问题:屁屁,甘肃是兰州省的吧?
大一时,大家都往网吧钻。咪哥虽然阳春白雪,但也偶尔下里巴人一回。有次我和屁屁进入网吧,正好咪哥在网上聊天,只见他摊开新华字典,极其严谨认真,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在键盘上戳,细致得像在绣花。期末考试后,全班就咪哥一个人英语不及格,大学四年,更是逢英必挂。
显然,要想知道viagra的含义,找咪哥是无解了。求人不如求己,我从埋头苦读的咪手里抢过英汉词典,看见上边这样的解释:viagra,中文名:万艾可。美国辉瑞研制开发的一中口服治疗ED的药物。
我操!原来是伟哥呀!
2.
伟哥是我同村好友,住的地方离半坡就几步路,小跑三分钟能到,出门喊一声也能听见。伟哥比我略长三两岁,小时斯斯文文,声音细声细气,温柔得像个邻家姑娘,从没和近邻长辈闹过矛盾,也没和同学吵过一句,长大后也一直保持着低调奢华的朴实形象,没穿过奇装异服,没有高端大气上档次沦为杀马特贵族王朝之流,口碑在小小的村庄里,可谓好得一逼。
伟哥的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父亲农闲时在黔(江)石(柱)公路边经营着一个砖窑,牵着一头老水牛踩瓦泥,从谭家沟运来煤炭烧制砖瓦。伟哥兄弟俩幼时也经常在砖窑帮忙,挖泥、割坯、出窑。
3.
半坡是一个偏远的山村,在渝鄂的交界线上,距离重庆黔江、彭水、石柱与鄂西利川差不多等同距离。
交界线就在背后的茶山脊梁上,放牛的孩子们经常在山梁上和湖北的放牛娃对骂:湖北佬儿恶又恶,顿顿都吃苞谷坨;湖北佬儿讨卵嫌,顿顿都吃苞谷面。
年幼的伟哥,举目四望,除了山还是山。在放牛、割草、砍柴、帮忙做农活的嫌隙,他迷茫地想知道,山那边是不是还是山。
95年左右,伟哥读初中。那时南下务工潮已经如火如荼,伟哥看见一些打工返乡的成功者穿得花花绿绿,心中慢慢萌生了梦想,也给自己定了几个小目标:
一是顿顿都能吃上烧白,二是给爷爷称几斤叶子烟,三是能让烧砖瓦的老汉不至于那么辛苦。
于是,伟哥把牛拴在坡上,把背篼一扔,就带着两个小伙伴徒步沿着黔石公路进发。是的,他们连广东在哪个方向都不晓得。
盛夏的黔石路,砂石滚烫,偶有方圆车路过,尘土漫天。
伟哥们的解放鞋,后跟都磨得见底。一路只有喝山泉水,偶尔地里拔两个红薯充饥。
他们此行并没有到达广东,只是走到了石柱马武,看见那里种烤烟有人招工,一块钱一天,于是他们决定停留下来,积攒够路费之后再向梦想进发。
4.
路费终究没有集齐,几个逃学的少年,就被父辈找了回来,一顿打骂之后,继续去上学,继续面朝大山,喂牛劈柴。
偶尔一天,伟哥在小镇的连湖大桥上偶遇同村一哥们,那哥们的父亲在广东务工,正好给他邮寄了几百生活费来,伟哥借了三百,踏上了南下的中巴。
伟哥满目憧憬地看着窗外,对于身后渐行渐远的山村,似乎也没太多不舍。
背井离乡,人生地不熟,在打工初期自然会面临各种窘困。文化程度不高的南下务工者,有去石场抱吆二三的,也有去煤矿挖煤的,还有去偷高压线的,也有去抢劫的。村里一个哥们给讲起他的抢劫经历,他说当时确实身无分文,只有铤而走险,我问:用啥子抢劫也,用刀子么?他哈哈一笑:徒手抢劫撒,连买刀的钱都没有嘛。
伟哥是好孩子,虽然伟哥没有去布鲁弗莱和纽易斯特等名校深造,但还是与挖机结缘,并且熟练掌握了技术,投身于深广建设,在繁华的珠三角,在霓虹闪耀的城市边缘,操控着冰冷的机器,为城市刨开一铲铲土石。
第一次结工钱时,老板给挖机上的他抛来一叠钞票,伟哥说:囊个这么多哟?不要不要。又把钱抛了回去,如是再三。
5.
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伟哥决定转行,开始经营酒楼,生意还算红火,他的那些小目标早就实现了。虽然年纪轻轻,但当地一些有头脸的都会叫他一声伟哥。
2000年左右,伟哥的父亲搭乘货车去谭家沟运煤,山路颠簸,司机开得飞快,在一个急弯时,伟哥的父亲被颠了下来,头撞在石头上,再也没有回来。
丧父之痛,对于一个多愁善感的男孩来说,是不小的打击。
伟哥说,他那一段时间里,什么都不想做,也不想说话,不想与人交流。他关了酒楼,有时身上一块钱都不带,就漫无目的在街头走,或者随便坐上一辆车,随便找一个站下。
然而,家里还有母亲,还有一个小兄弟,伟哥还是很快振作起来。长兄如父,腼腆文静而青涩的伟哥,像踩瓦泥的老水牛一样,默默地挣钱给家里开支,供兄弟读书,稚嫩单薄的肩膀扛起了一个家庭。
6.
我读大学时,可能见我是生产队第一个考上大学的,也许还因为彼此都是苦孩子,伟哥虽然在千里之外的广东,对我频频关照,经常给我充话费,还给我存过好几次生活费。
一个寒假,我回到老家,适逢伟哥堂妹结婚,我在他们院里帮忙记人情,恰恰有一个亲戚也办酒,我想晚上去一趟。那亲戚在邻乡,走路至少两个小时,于是,我和伟哥借了摩托,伟哥载着我前往。
冬日里,略微有些寒冷,我把手伸进伟哥荷包,嘿,里边赫然一枚杜蕾斯,当然,还可能是冈本……原来伟哥耍朋友了!
那晚我们最终没有找到那亲戚家,但我依然觉得,一个小兄弟需要去做一件事,伟哥能够去帮忙借摩托并冒黑前往,有些古道热肠的意思。
7.
伟哥耍的朋友,是同村的一个妹子,当时在重庆读大学。
为了离家近一点,也离女友近一点,伟哥从广东回来,在北碚襄渝铁路复线工地上修隧道。
我开学时坐T9去北京,要经过伟哥工地外边,经常提前给他打电话。火车过嘉陵江桥后,穿过几个隧道,北碚黄桷的老街呈现在眼前,这里,伟哥可能经常携手和他的恋人走过,抑或走过街角,点二两牛肉面。
印象中我没有对伟哥荷包里的套套动什么手脚,显然,伟哥喜当爹这件事,是他们自己的功劳。不久,他们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
8.
时至今日,我依然没有觉得他们的爱情也好,婚姻也罢,没有什么不妥。每个人都拥有爱与被爱的权利,与你是农民工也好,大学生也罢毫无关系。
爱情是头猪,婚姻是么子也,婚姻可能是红烧肉。有猪无猪无关紧要,人的一生不能缺少红烧肉。
酉水闲人说:婚姻那个东西,看得见,摸得着。有早晨有下午,有寒冬,有酷暑。就是没得风花雪月,没得海誓山盟。只有两个人带领一支队伍,对日子作战,对身体作战。自己埋葬自己。
或许是千里相隔聚少离多,也或许是因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冲突,伟哥的婚姻最终走到了尽头。
他给我打电话,说了很多,虽然我大多都记不得了,但我大致记得,他说他想对她好,想奋不顾身去爱她,可惜再也没有机会了……
9.
或许,伟哥经常在夜深人静时,自斟自酌,独自品尝岁月这杯苦酒。
他的空间记录了一些他的心路历程:
似水流年、无处安放的情感,烦了一个人藏、病了一个人扛、痛了一个人挡、路上一个人想、街上一个人逛、晚上一个人的床…习惯了一个人的生活,变得沉默变得冷落没了理想、不想说不想看,不是高傲也不是放逐,只是厌倦了那些随时可能失去的寄望……
有时觉得,伟哥更像是一个诗人,他站在岁月的河岸,向自己的过往打几个水漂:
时间在点点滴滴中流过,挥霍寂寞,我的选择在现实的沙漠中干涸,希望在凛冽寒风中奔波,理想在物欲横流中消磨,怎能逃得过,慢慢蹉跎,能是谁的错,但愿所有的付出,能有个好的结果!
10.
半生浮沉如梦,伟哥开始思考自己的未来,如果继续去开挖机,似乎也不是个出路,不如做点小本营生,能养家糊口,说不定还能开辟出点儿天地。
经过几番思量,伟哥决定做沙县小吃,对于心灵手巧且开过酒楼的他来说,自然不是难事。
他的店就开在老家县城滨江路边上一个角落里。对于无辣不欢的重庆人来说,沙县小吃自然是淡出个鸟味来,何况县城里的人更习惯当地一种特色小吃——米粉。因此,伟哥的店门庭冷落,生意寥寥。
一日,几个彪形大汉进入,伟哥喜出望外,问:客官,来盘么子?
大汉答:来盘营业执照。
后来,伟哥又将店开到乌江对岸的山谷公园附近,生意依然没有什么起色。
11.
几年前,我端午回乡,在半坡呆了几天,出来时经过县城,在城北隧道下车,给伟哥打电话,伟哥喊过去尝尝他的手艺。上午去小镇给外婆买药,到彭水已下午三点,时间已经不早,本不想再耽搁,准备去外河坝坐车上重庆。电话里我说:饭就不吃了,我明早机票比较早,下次再来和你聚嘛。快挂电话时,我说:我操,我还是过来看下你,实在舍不得就这么走。
我带着我的盲人叔叔,搭乘两个摩的,到了水务局跟前,举目四望,找不到传说中的伟哥沙县小吃。
伟哥从街角出来,微笑着招呼,依稀是当年那个略微腼腆的少年。
门店不大,招牌也不显眼。我们走进店内,伟哥热情地端出馄饨,以及一盘红烧肉,并特意给我一盅他煲的杜仲牛鞭汤。
我在吃馄饨的时候,抬头看见了墙上一张小照片,那是他的前妻和他的女儿。
12.
一晃几年就过去了,现在和伟哥都疏于联络。只是晓得他辗转在广东和江西做面食,做的是风靡全国的重庆小面。前几天打过电话,他说生意还可以,也赚不了太多钱,之前在广东还亏了不少。
有时想来,可能自身底子太薄,身边伟哥这样的朋友不少,有过梦想,也曾努力奋争,但依然过得不尽如人意。
或许,烦恼太多,未来太远,梦想太飘渺,搞得我们垂而不举,举而不坚,坚而不久……这个时候,伟哥,就把馄饨或者小面当做viagra服用吧,更何况,你还有杜仲牛鞭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