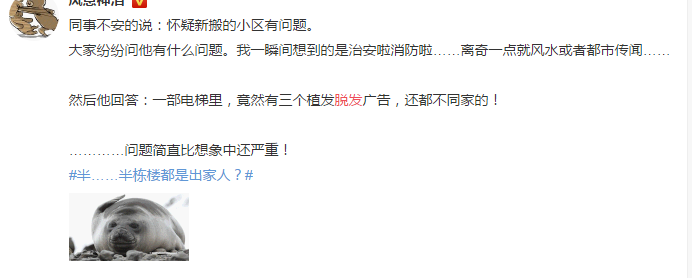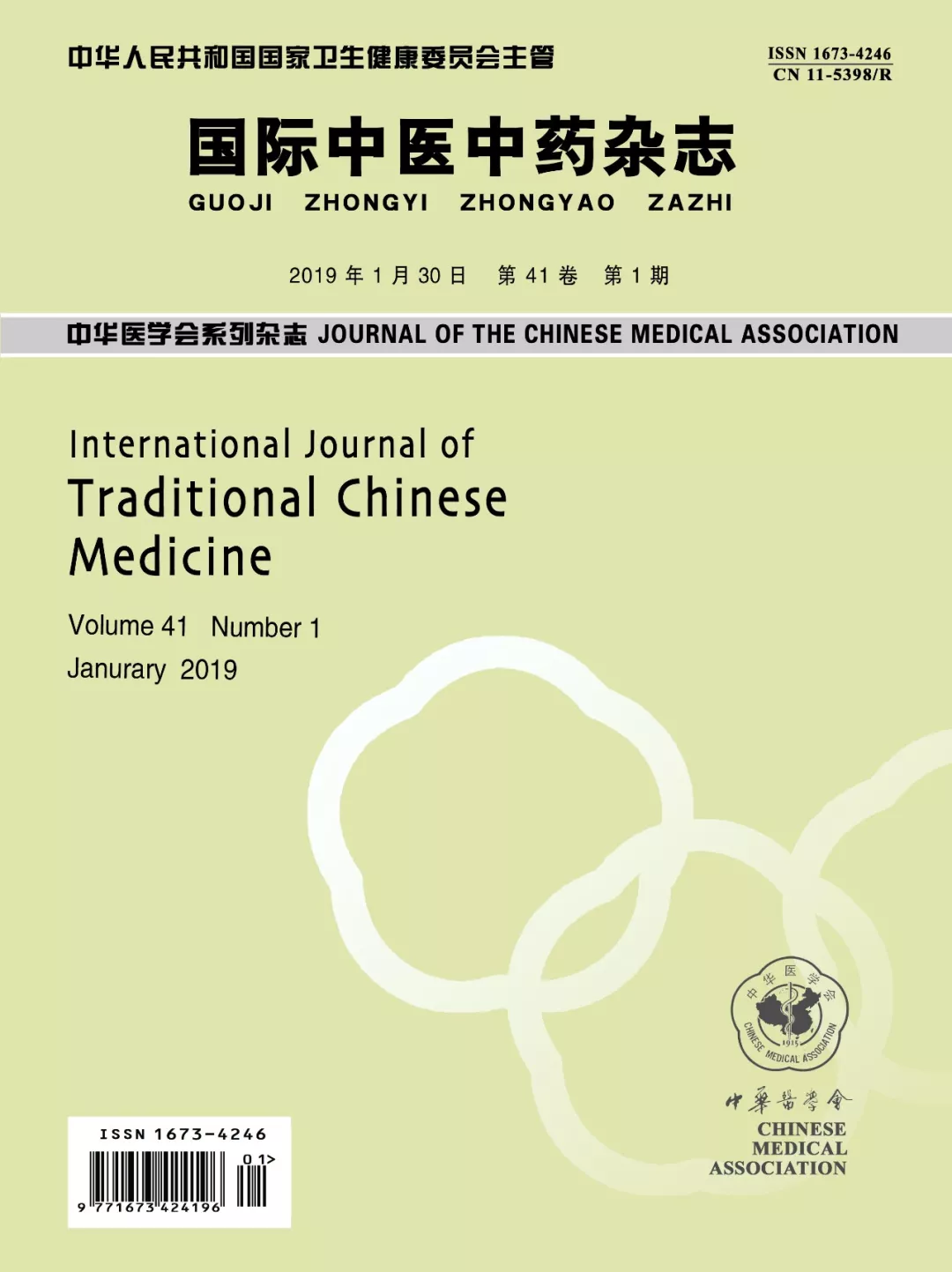姥爷,胰腺癌,汉堡包。
姥爷的帽子
姥爷走了。
我们凌晨赶到的时候,屋里人很多,但没有哭声。
舅舅们在床边烧着纸钱,姥姥在客厅叠着金元宝……所有活人都沉默地忙碌着,偶尔小声交谈。
角落里姥爷的手机还在充电,重复唱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除此之外,聒噪的只有火焰和夜风。
姥爷穿了一身新,仰面躺在床上,头底下枕着弟弟盖过的小花被。灵前供着酒、水果,还有他生前爱吃的大桃酥。
在过去的近三个月里,姥爷都虚弱地蜷缩在大床的一角,一天天熬着。现在他终于能舒坦地平躺了。
我握住他冰凉的手,发现手里松松地握着两个蛋黄果子,中间夹着一枚一元硬币。
按我家乡的习俗,去世的人下葬前要在手里放上钱和粮食,这样去了那边才不愁吃穿。我试着帮他把手心合上,但姥爷的手还没有僵,根本攥不住。
我妈说,你念叨念叨,你说,姥爷,拿着吧。
我说我不信这些。
坐在床沿,我用力攥住姥爷的手,十分钟,半个小时,或者更久,直到我的手也没了力气。
松手的那一刻我的脑子空空荡荡,心想,这就是最后的告别了。
灵桌上的糕饼
姥爷打我记事起就一直在吃药。他行动迟缓,反应迟钝,总是痴痴傻傻的,看起来需要很多照顾的样子。
我妈还给他起过外号,叫慢吞吞。
脑血栓加上高血压,慢吞吞不能吃海鲜,酒只有过年过节的时候才能喝上一点点;
慢吞吞的肠胃也不好,饮食上也需要特别注意,太油太辣都不行,大鱼大肉也要少吃。
偏偏慢吞吞生前最爱吃的就是各种垃圾食品:
好利来的豆腐蛋糕,惠诚的曲奇饼干,肯德基的香辣鸡翅,茶百道的招牌芋圆奶茶,还有街边点心铺里称斤卖的桃酥……
其中他最爱方便面,我妈不准他吃,他就经常自个儿趁着遛弯买个一两包,偷偷藏在厨房里。
确诊胰腺癌的那天,医生把我妈拉到病房外头,话说得很直白。
晚期,癌症已经扩散得哪哪儿都是了,考虑到姥爷的年纪,手术台上得去下不来,还是尽早准备后事吧。
当时,姥爷应当是什么也不知道的。
他躺在病房里头,突然说想吃汉堡包。于是汉堡包给他买来了,已经一个多月吃不下饭的姥爷坐在病床上,一口气吃掉了半个。
我妈说过,姥爷一点儿也不傻。看着动作慢,但是脑子灵光得很,他什么都清楚,只是不爱说。
所以我猜,即便家里人一致瞒着他,但姥爷从确诊那天起就已经知晓了大概。
也许他没猜到胰腺癌这三个字,但他已经猜到了之后的所有。
于是姥爷出院了。出院后每天只能喝下一点米汤,脸颊和上身迅速消瘦,腿脚却异常浮肿,把宽松的睡裤撑得鼓鼓胀胀。
不久之后,突然发病的姥爷就被连夜送回了盘州老家——我妈姊妹四人生长的地方。
得知这个消息时我正在高铁上,那趟车从成都开往贵阳,途径眉山。
眉山是座很美的城。我站在眉山站台上抽了半根烟。
远远望,城里是屋檐绿意,城外是麦苗青青。离离彼黍,姥爷也会成为其中之一吧。
停在厨房的轮椅
再次回到老家,姥爷已经瘦脱了相,有气无力地坐在轮椅上。
家里人轮流推着他在屋里转悠。奈何房子实在太小了,多一个人都转不开身。轮椅推来推去也只能小幅度地前后晃悠,像是超市门口的投币摇摇车。
老家的盛夏,短袖能拧出水来的天气里,姥爷穿着棉睡衣,全身冰凉。姥姥怕他冷,拿了我儿时的小毛毯,缝上两根绳儿,给他系在脖子上。
这时姥爷的口腔内部几乎全部溃烂,时不时就会有坏死的组织从嘴里落出来。别说是饭菜,药、水、果汁、牛奶、汤……全都已经喂不进去了。
即便如此,姥爷依然清醒。
虽然所有的器官都已经濒临衰竭,甚至周身已经开始散发出微微的腐味,但姥爷的眼神依然澄澈,看上去甚至比他患病前还要亮些。
我握住他的手,唤他姥爷。
他回握我,嘴唇上下翕动,用口型念我的名字。
应该就是这两天的事了,我妈小声说,你姥爷在等你大舅呢。
大舅远在珠海,要1号晚上才能赶得到。家里人担心他可能赶不上,当天下午就用姥爷的手机给他打了视频电话。
看见大舅的脸,姥爷明显有些激动,眼睛瞪得老大,从咽喉里发出嗬嗬的叫喊声。这下大家的情绪都有些绷不住了。
筹备葬礼是件极繁琐、伤神的事,人一忙起来就很容易忘记:叫人落泪的从来不是生命的终止,而是生命的消逝——生命,在各种意义上的,必然的消逝。
爸,你微信里的钱转给谁?
挂了大舅的电话,我妈问姥爷:转给我妈,成吗?
姥爷应了一声。
好了,你看,我妈把转账界面送到他眼前,
转好了已经。
姥爷轻轻点了点头,又合上了眼睛。
爸,我妈她以前总跟你吵架,我妈轻轻抚着姥爷瘦削的肩臂,……你别想她。
我妈哭了。
姥姥的背影与灵堂里的人
送葬那天是个大晴天。
姥爷身上盖着明黄的经被,被抬进了冰棺里。
临出门前我妈嘱咐我,一会儿送姥爷走的时候一定要哭,要大声哭出来。我还是说我不信这些。
挤几滴眼泪出来,或者干嚎两声,这并不难,但我不想。因为姥爷已经走了。
就在守灵那晚,当我紧紧攥着他的手,却意识到他再也不会回应我的那一刻,我就知晓,姥爷已经永远地离开了。
所谓的身后事,都是做给活人看的。
哭,当然也是哭给活人听的。
可能活人就是比死人更需要哭声和眼泪吧。
然而灵堂里的气氛却与悲痛毫不相干:
纸扎花圈和赛博电子花圈并肩屹立,黄白塑料花与喷绘松鹤图相映生辉;高价请来的道士们吹吹打打左蹦右跳,道符恨不得贴到观音脑门心上,佛的道的阴阳的一锅全端。
灵桌前的火盆里噼里啪啦地烧着纸钱,灵桌旁的空地上稀里哗啦地搓着麻将,烟灰裹着火屑四处飘洒,瓜子壳橘子皮散落一地。
我陪姥姥坐在灵堂一角,茫然地看灵堂里外的人们团团围坐,唠着邻里邻外家长里短。谁家孩子高考考砸了,谁家孩子年底结婚了,谁家老人生病住院了,谁家两口子早就离婚了……
看得久了,我甚至开始怀疑,其乐融融和欢声笑语才是葬礼该有的主题。
期间姥姥哭了一次,一群人围上来,七嘴八舌地劝。你想开点,你别哭了,一把年纪了,小心哭坏身体。
但姥姥哭得更厉害了。
我懂她的无助。
得病的这三年,同样的话我也听过无数遍,你想开点,开心点,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言下之意是,你可别再给我们添乱了。
姥姥只哭了几分钟,但那几分钟漫长得像几个世纪。
她哭得上气不接下气,胸背剧烈地起伏着,人们七嘴八舌的劝慰都盖不住她的哭声。
至少在那几分钟里,这世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愈合姥姥的悲恸。
我搂着她的肩膀,轻轻拍着她的手臂,就像小时候她哄我入睡时那样。我说,姥,你哭吧。想哭就哭吧。
而除此之外我什么也做不了,什么也做不到。
生活是无论如何都要继续的,这谁不懂呢?
姥爷走之前,姥姥就常说,生老病死,都是没法子的事,换谁也躲不过。
姥姥比在座所有人都想得开,但她已经老了。相伴多年的人离开后,一个老人难道连伤心都不被允许吗?
我不能理解。我感到愤怒,但这愤怒又无法指向任何一处,因此一文不值。于是我感到无力,我无力叫停这荒诞的一切,只能期盼它快些结束。
观音像与公路
火化下葬,依然是大晴天。
家里人担心姥姥受不了,坚决不让她去看。而我也怕自己当场发疯,出门前一口气吞了三片丙戊酸镁。(抗躁狂的药
开药的时候医生特意嘱咐过,这药是治癫痫的,不能多吃,一天最多三片。现在想想,我后悔了,当时就应该把那一瓶药干了才对。
姥爷的墓选在了县城郊区的山上,风景很好。
菩萨像就立在墓边,脚下是绵延的公路和苍翠的山岭,远处的市集隐约传来嘈杂的叫卖声。
火化很快就结束了,一个半小时不到。
姥爷的骨灰被装进昂贵的骨灰盒里,由大舅抱着前往墓地下葬。在等待道士做法期间,骨灰盒被暂时安放在墓碑旁的花坛上。
我在那楠木盒子旁边坐下,手里撑着一把混乱中谁塞过来的黑伞——有说法是骨灰不能见阳光。有些支离破碎的记忆在这时从眼前一闪而逝,关于我的姥爷。
比如,我的姥爷最喜欢收集的是手电筒,最喜欢戴的是老头贝雷帽,最喜欢听的是凤凰传奇的《荷塘月色》;
比如,我的姥爷送我上小学,最喜欢在河边桥洞前的小摊上买一份报纸;
比如,我的姥爷最喜欢捣鼓智能机,虽然他总是搞不懂,而我总是不耐烦跟他解释……
再比如,我的姥爷有一双大手。我从那大手里拿过糖,拿过月饼,拿过小圆饼干,拿过不少零花钱……
我的姥爷走后,那双大手冷得像冰。
但这些,现在都不重要了吧。
记忆还在,但记忆的主角已经归于尘埃。于是这记忆无法再得到补充,最终也抵不过时间的消蚀,归于虚无。
真令人心碎。
我摩挲着骨灰盒上繁复的雕花,心想,像姥爷这么时髦的老头,才不会稀罕这种老古董呢。
道士们还在画符念咒,家人们还在烧纸上香,引灵的大公鸡被拴在墓边的柏树上,警惕地环顾着四周——这场葬礼还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墓前又升起了袅袅青烟,纸钱冥币金元宝,都在熊熊烈火中迅速化为灰烬。
留给我心碎的时间也不多了。
就在这一片忙碌中,有个眼生的中年人突然走到了我的面前,煞有其事地说,这伞不能女孩儿来打,换你弟弟来。
这可真是搞他爹的大笑了。
为什么?我直直地盯住他的眼睛。
不为什么呀,女孩儿打伞不好的。
他有点急了,神情中还带着些不解,仿佛这规矩是全天下万古不变的共识,就我一个人不懂。
你谁啊?你算老几啊?这是我姥爷。
我当然也急了,我妈听了赶紧上来拉住我,让我听叔叔的话,换弟弟来打伞。但我紧紧地握住伞柄,一步都不让。
气氛立刻僵持了起来。
在场的人不算少,大家都选择沉默,好像他们在女孩儿不能给骨灰盒打伞这件事上早已达成了一致——没有商量的余地,不行就是不行。
但总之,没有人愿意站在我这一边。
那一刻,接连几天都挤不出来的眼泪一瞬间全涌了上来。我忍不住想,姥爷一向宠我,如果姥爷还在,他肯定会向着我。
可是姥爷已经不在了。
滚开,我把眼泪生憋了回去,让自己尽量清楚地吐字:所有人。
我妈拉着我的手臂,问我是不是要把她气死。滚开。我盯着她的脸,又重复了一遍。
后面一句我没说出来:不然我让你们所有人给姥爷陪葬。
不是要视死如生吗?不是要风光大葬吗?你们这么爱姥爷,不如一起下去陪他吧。
我当时真是这么想的。
反正我早就疯了,不吃药说不定早就死了,死前多杀一个还是一群,对我来说差逑不多。
这场给姥爷办的葬礼,从头到尾都在刻意忽略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姥爷已经走了。
他死了,他不存在了,他的身体化作一把骨灰,他的思想、精神、心灵也随之覆灭。
He doesnt matter anymore.
在这样的终结面前,活人能做的并不多,惟有告别和怀念而已。我们倒好,非但要把死人灵肉分离,还要把那灵捧上神坛,要求它多行方便,给予活人利好。
可怜我的姥爷,超度前只是个病重时依然惦记着汉堡包的普通人,超度后却被迫成了某种负责保佑后人汉堡包永远吃不完的神灵。
这算你妈哪门子的解脱?
末班高铁的站台上空空如也
葬礼结束后,我在回程的高铁上给姥爷发了很多短信。在此之前,我甚至连他的微信都没有加,而现在一切都太迟了。
销户之后他的微信会被注销,再也不可能收到我的好友申请。
处理完姥爷的丧事,姥姥和舅妈住回了盘州老家,家里人该工作的工作,该上学的上学。
一切如常,一切照旧,生活照旧向前滑行而去。而姥爷就这样从我的生命中消失了,轻飘飘地,就好像从未来过。
奇怪的是我,吃着药还是整夜整夜地失眠,只有在姥姥姥爷住过的房间里才能勉强入睡,一睡就是十七八个小时。
每次从昏睡中醒来,都会陷入某种怔忡之中——屋子里的人已经离开了,但屋子里满满的还是有人住过的痕迹。
床边是姥爷用过的躺椅,柜子上是姥姥的护肤品和药,衣柜里是姥姥姥爷的冬衣棉鞋、老旧的床单被套,还有我和弟弟小时候用过的背带……
被这些物件围绕着,恍惚间会觉得,姥姥姥爷还在我身边。只要我推开房间门,就能看到他俩买完菜回来,一前一后地吵着嘴进门。
姥姥说,家里又不是没纸,你干啥又买那么多?姥爷回嘴道,多买点怎么了?不让我买我偏买!
有时候,这些幻象实在过于逼真,我甚至会在睡梦中一骨碌爬起来穿衣服,只因为听见了他们开门换鞋的声音。而后又会很快清醒过来,像个木偶一样站在门口发呆。
天知道我有多恨这些醒过来的时刻。
最后。
打下这行字时,是凌晨5点39分。
一般这个点,姥爷早就起了床,在客厅里来回晃悠了。而我刚刚勉强熬完一个通宵,正在思考这篇文章该如何收尾。
应该说,或许,我可以做到沉着而冷静地消化死亡这个命题,但我永远无法真正地告别姥爷,至少不是通过一场喧闹的葬礼这样的形式。
一个人成长的过程也是意识成型的过程,而我从小在老人身边长大,姥姥姥爷这四个字早已内化为我仅有的情感支撑中最为坚实的那道防线,包含着我对爱最原初、最本真的理解。
现在,这道防线塌了一半,我心里的楼宇也跟着塌了一半。
我这才意识到,它从来就不是坚不可摧的,我必须重新垒砌起属于自己的城墙。
6点整,天色蒙蒙亮,耳机里还在循环着蔡琴阿姨的歌:
鱼儿离不开这片大海,
人儿还在等着他回来。
鱼儿从不回答,
我要如何不想他……
我要如何不想他呢?不清楚。
目前我能想到的回答可能只有,以后少吃汉堡包吧。
文/影 甘小付
乐 我要如何不想他-蔡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