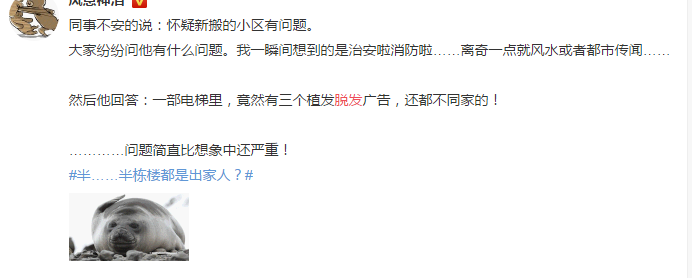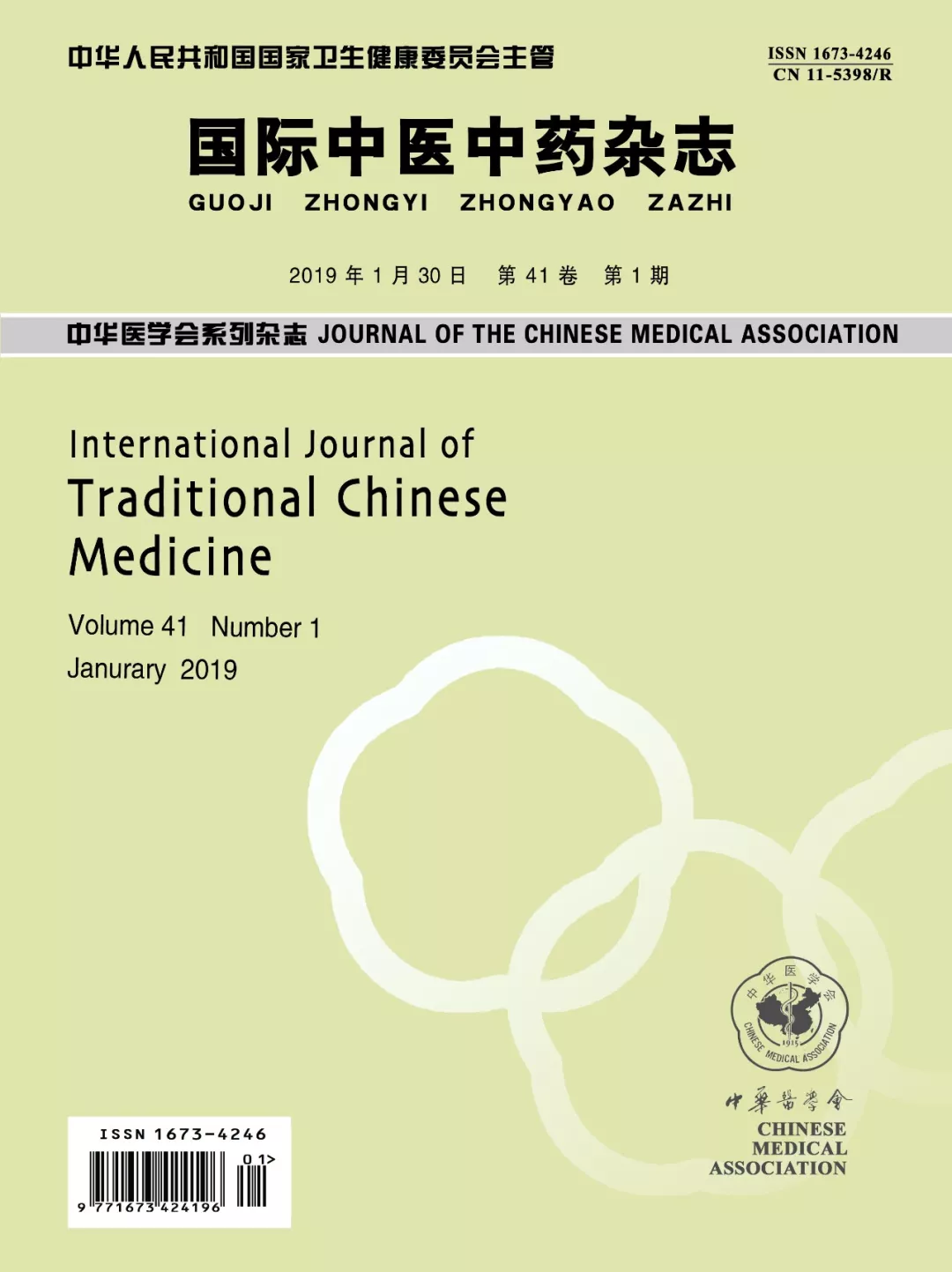我是怎样发现CT检查会加快癌症进展的(上)
十年磨一剑之作(2)
2016年8-9月以《一次复查捅了马蜂窝》为题首发于新浪博客
2023年5-11月修改补充
八年前,确切地说是2015年5月20日前后,我去医院做了一次例行复查,项目有CT胸部HR平扫(5月18日)、肝脏磁共振平扫(5月20日)、头部磁共振平扫(5月22日)和肝肾功能常规。令我没有想到的是,这次复查就像捅了马蜂窝,导致一直控制良好的肿瘤急剧恶化,使我差点没能活过当年。
当时,距离我的黑色素瘤复发后全身转移已经五年又一个月。在这五年出头的时间里,通过现学现卖的纯中医自我治疗,我的肿瘤虽在进展,但速度由起初的飞快变得较为缓慢,似乎我开给自己的中药使癌细胞处于半休眠状态。
这次复查结束几天后,我感觉人有点不大对劲,但又说不清是什么。作为一个晚期癌症病人,身体有点不对劲是很正常的事,因此我没在意。但到6月上旬,也就是复查后两周左右,轻度的不对劲变成了明显的异常,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以前胃口一直很好,在单位食堂吃饭时,我的饭量比那些20来岁的健康小伙子还大,现在却突然没有了食欲,到了饭点也不再有饥饿感,无论吃什么都没味道。(2)以前一直偏胖,170cm的身高保持在80公斤左右,现在则明显瘦了一圈。
上篇图1 本文初稿于2016年8、9月发表于新浪博客:
此时我仍然没有多想,本能地以为食欲不振和消瘦是我开给自己的中药药量太大,时间一长损伤了脾胃所致。于是我将药量减少了三分之二左右,并添加了一些开胃消食药。这样服了近十天,症状毫无好转,反而仍在加重。我就觉得问题不在于药量太大,很可能是五年来肿瘤的进展速度虽然明显减慢,但毕竟仍在进展,癌细胞不断增殖,量变导致质变,最终发展到控制不住的地步。对晚期癌症病人来说,这种情况很难避免,也无法解决,我能做的就是适当加大药量试试。
然而情况仍无好转,没过多久还出现了腹痛和后背疼痛。腹痛是2010年6月(发现复发转移两个月后)就有的,其根源是胆囊转移,当时我在省内找了三个名中医都没有效果,无奈之下开始自学中医给自己治疗,不久后腹痛消失了。随后几年,腹痛有过几次反复,但都不严重,通过调整中药很快解决了。至于后背疼痛,是多发骨转移造成的,始于2011年8月,经调整中药两个月左右后基本缓解,在次年有过一两次反复,但不严重,短时间内便恢复正常了。从2012年秋天到这次复查前,超过两年半的时间里,我一直没有癌痛等肿瘤相关症状,生活质量接近健康人。这样的疗效对存在肺、肝、胆囊和骨转移的晚期黑色素瘤来说,无疑是前所未有的。然而现在,如此出色而稳固的疗效竟也突然反弹了!并且,在药量加大后,癌痛不但没有减轻,反而仍在加重。有些部位虽然没有疼痛,却像有什么东西时不时在轻轻地刺你,有时又像是有蚂蚁在爬——这是癌细胞高度活跃的表现。现在整体的感觉是我身上的癌细胞已经疯了,它们到处作乱,而且势不可挡。我当时对病友这样描述道。
在这种情况下,我再迟钝也觉得不正常了,于是开始了认真的思考:我的中医治疗效果一直很好,在全身转移的情况下带瘤生存五年,且已经连续两年半没有肿瘤相关症状,过着与健康人相差无几的生活;但是现在,癌细胞却突然疯长,进展速度比我刚发病(1993-94)没有治疗时还快得多,食欲丧失、身体暴瘦,消失已久的腹痛和骨痛卷土重来,加大药量一些日子后症状丝毫没有减轻、反而仍在加重。这究竟是什么原因?我的整个治疗都跟以前一样,没有任何改动;我未做西医治疗,不存在耐药后疗效急剧反弹的可能;我的生活也没有任何变化,既没有增加什么,也没有减少什么,饮食起居一直都很注意,没有丝毫放松——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为什么肿瘤会突然爆发式进展?我绞尽脑汁苦苦思索,却依然茫无头绪。
7月上旬的一天(距离那次复查大约一个半月后),我正在某三甲医院的自助机上挂号,突然想起了几天前该院放射科一位女工作人员的几句话:当时我在替父母预约肺部CT,这位工作人员对我说,他们会用那台新的CT机替我父母检查,新机器看得更清楚,辐射也更小。我听后还有些疑惑,心想她应该是随口说说的吧,因为以目前的科技水平,CT机想做到成像更清楚、辐射却更小,似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我没有细想,转头忙别的事情去了。然而现在,毫无来由地,那位工作人员的话突然冒了出来。我楞了一下,紧接着脑子里电光石火似的闪过一个词:辐射!
对,就是辐射!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这段时间我的治疗和饮食起居虽然没有变化,但我做了一件已经整整三年没做的事:CT检查。检查时摄入的X射线是一种能够致癌的电离辐射,一定是它刺激了癌细胞,使我肿瘤的进展大大加快了!
想到这里,我的大脑开始高速运转,与此相关的念头一个接一个不停地冒出来,然后便是不断的分析,推理,质疑,解答……。不过,几十分钟后,我的思绪已经理清。
回到家后,我通过搜索神器Google查找国内外学术文献,主要想看看有没有关于CT等检查的电离辐射刺激癌细胞加速进展的报告,结果并没有,只找到一些辐射给健康人带来危害、包括使他们患上癌症的文章。但我没有因此而怀疑自己的观点,相反,我依然相信,我这次异乎寻常的肿瘤加速进展是CT检查时摄入的X射线导致的。这除了不存在加快肿瘤进展的其他可能性外,还是因为从将近一百年前开始,放射线就被公认为是一种致癌物质。1895年11月8日,德国物理学家伦琴(1845-1923)在做实验时偶然发现了X射线(又称伦琴射线)。他随即将这一发现公之于众,轰动了欧美科学界。在次年的头几个月,X射线已开始被应用于医疗诊断等领域,甚至几乎成为一种时尚(例如X光试鞋机,X光艺术照)。当时,人们尚未认识到放射线的危害,没有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因此,X射线的广泛应用酿成了医疗放射学史上第一波悲剧,大批民众的健康受到严重甚至致命的损害,最早一批放射工作者更是几乎全部殉职,他们大多死于癌症。1936年,德国伦琴学会在汉堡圣乔治医院替殉职的放射工作者设立了一座各国X射线和镭牺牲者纪念碑(Monument to the X-ray and Radium Martyrs of All Nations),以纪念世界各国那些在与人类疾病的斗争中被X射线等放射性物质夺去生命的医护工作者和科技人员。当时刻在石碑上的人名共有169个,后来增加到359人。如果把医疗以外的领域(例如核武器、核电站)也包括在内,那么因从事放射工作而失去生命的人就更多了。
上篇图2 国外网站上关于各国X射线和镭牺牲者纪念碑的其中一则介绍:
在这些殉职的放射工作者之中,令我印象最深的有以下几个:
·发明大王爱迪生的助手戴利(Clarence Madison Dally, 1865-1904)。戴利在替爱迪生工作时,常常在没有任何防护的情况下,一次次把手放到X射线源与荧光屏之间,遭受了大量的辐射。一段时间后,他的头发、眉毛和睫毛掉光了,脸上全是皱纹;他的左手被射线灼伤,肿痛严重,改用右手工作后,右手也被射线灼伤,只是程度比左手轻一些。他跟当时其他放射工作者一样,以为情况并不严重,慢慢就会痊愈,但他想错了。几年后,戴利手上的伤恶变为癌症,切除整条左臂和右手四根手指后仍阻止不了癌细胞的进展。1904年,距开始接触X射线(1896年)八年多后,戴利因癌症扩散去世,年仅39岁。他被视作第一位殉职的放射工作者。
戴利的悲惨遭遇令爱迪生触目惊心。爱迪生曾在多次操作自己刚刚制造出来的X射线设备后发现视力受损,差点失明。他本能地预感到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照着不痛不痒的新射线背后隐藏着未知的危险,于是及时止步,不再接触放射线。不过,当时他对放射线危害的认识还比较粗浅,直到看到戴利的辐射损伤越来越重并最终导致死亡,他才意识到问题比他预料的严重得多。为了保命,他停止了一切与放射线有关的研究,并终身拒绝接受医用放射设备的检查。有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他心有余悸地说:别跟我谈X射线!我怕它……我也怕镭和钋,我不想搞这些。可以说,戴利的死促使爱迪生及时逃离第一批放射工作者的队伍,避免了与他们一起殉职。1931年,爱迪生死于糖尿病并发症,享年84岁。
上篇图3 爱迪生(右)透过自己设计的荧光镜,观察着助手戴利处于X射线照射下的手:
·居里夫人和她的大女儿大女婿。居里夫人即玛丽·居里(Marie Curie,1867-1934),因在放射性领域的研究成果及发现放射性元素钋和镭,一生两次获得诺贝尔奖。她于67岁那年死于再生障碍性贫血,病因被公认为是长期、大量的放射线摄入。
上篇图4 2020年11月8日,诺贝尔奖官方推特发表推文称,居里夫人1899-1902年间使用过的实验笔记本至今仍具有放射性,且这种放射性还将持续1500年:
居里夫人的大女儿伊雷娜·约里奥-居里(1897-1956)与其丈夫让·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里(1900-1958)也以研究放射性物质为毕生的事业,夫妻俩于1935年同获诺贝尔化学奖,且后来都因长期的辐射暴露而早逝:妻子于59岁那年死于白血病,丈夫于58岁那年死于肝癌。
·美国放射学先驱伊丽莎白·弗莱虚曼-阿虚海姆(Elizabeth Fleischman-Aschheim,1859/1867-1905)。她的姓氏为其娘家姓弗莱虚曼和夫家姓阿虚海姆组合而成(上文居里夫人的大女儿婚后的姓氏与此相似,当时她的丈夫主动提出,他们夫妻的姓氏除了按惯例沿用他的姓约里奥外,另外再加上他岳父岳母的姓氏居里,以向他们致敬)。她的出生年份有两个版本:1859或1867。
伊丽莎白出生于一个从奥地利移民美国的犹太家庭,到美国后生活在旧金山。她因家庭经济原因未上完中学,后来报读了簿记的培训课程。母亲去世后,她搬到姐姐姐夫家居住,并在姐夫的诊所担任簿记。
1896年,伊丽莎白读到了伦琴发现X射线的报告,对X线摄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姐夫的鼓励下,她参加了一个关于X线设备的公开讲座,又读完了一所工程学院为期六个月的电学课程。之后,她向父亲借钱购买了一台X光仪和一个荧光镜,并很快熟练掌握了各种不同X光设备的使用。
1897年,伦琴发现X射线一年后,伊丽莎白在旧金山建立了一个X射线实验室。除了给当地医生指派过来的患者拍片检查外,她还用X光仪检查食品有无掺杂杂质,并给动物和日用品(例如鞋子)拍片。
1898年美西战争结束后不久,伊丽莎白受美军委托,替从菲律宾战场经旧金山返回美国的伤兵拍片确定子弹或炮弹碎片在体内的位置,以帮助外科医生将其取出。
出色的X线摄片技术使伊丽莎白闻名遐迩,并受到专业人士的高度称赞。
1900年,伊丽莎白成为美国伦琴学会的创始会员,且还是该学会罕有的非医生会员。
伊丽莎白在工作时,跟当时所有同行一样,经常把自己的手放在荧光镜前以确定曝光时间。除此之外,为了打消人们的顾虑,她有时还会用X光仪照射自己,以显示这项检查并无痛苦。在长达七年的辐射暴露后,也就是1903年时,她的双手被射线损伤。限于当时的认识水平,她不知道这是X射线导致的,继续在无防护的情况下工作。1904年接近尾声时,她手上的伤恶变为癌症。1905年1月,在整条右臂连同肩胛骨和锁骨被切除后,她不得不告别X线摄影工作。几个月后,她的癌症复发,并转移到胸膜和肺。8月3日,在同行戴利(爱迪生的助手)去世十个月后,伊丽莎白也英年早逝。她是第一位殉职的女性放射工作者。她的墓碑上写着:我想我在这个世界做了一些有意义的事。
上篇图5、图6 国外网站上关于美国放射学先驱伊丽莎白•弗莱虚曼-阿虚海姆的介绍:
随着辐射损伤和死亡病例的大量出现,人们终于意识到放射线的危害,开始采取系统的防护。为了在世界范围内就电离辐射的防护提供全面的建议和指导,1928年,国际X射线和镭防护委员会宣布成立;1950年,该组织改名为国际放射防护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Radiological Protection, 简称ICRP)。
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辐射防护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如今,在医疗领域,不管是X线机和CT等放射医学诊断设备,还是PET-CT等核医学诊断设备,或者直线加速器和伽马刀等放射治疗设备,它们在设计制造时已充分考虑了如何减少电离辐射的问题,进入医疗机构后又照规范被安装在特定的机房,机房的墙壁和门都采用特殊材料,具有屏蔽各种放射线的功能;患者在机房接受检查时,工作人员在旁边的控制室内通过铅防护玻璃观察窗和对讲机进行操作,避免了辐射暴露;放射从业人员的职业辐射剂量被限定,并通过身上佩戴的个人剂量表加以监测……从患者方面看,他们接受放射学和核医学的检查治疗必须具有正当性,即只有在绝对必要或者说利大于弊的情况下才被允许;同时,他们重要的非照射部位必须做好防护措施,例如做胸部CT时至少应当用铅围裙保护性腺,做腹部CT时至少应戴铅围脖以保护甲状腺,等等。由于实现了防护最优化,现在从事放射职业是安全的,至少没有了生命危险,那座位于汉堡的殉职放射工作者纪念碑已经60多年没有增添新的姓名了;而对于接受检查和治疗的患者,电离辐射严重危害健康的时代也早已一去不复返了,他们对医疗辐射的担心常被医生视为杞人忧天。
从电离辐射的生物效应来说,机体遭受电离辐射后可产生两种有害效应:确定性效应和随机性效应。确定性效应是达到一定剂量后必定会发生的损伤,例如皮肤和眼睛的损伤。随机性效应指本人罹患癌症和后代患上遗传性疾病的效应,通常没有剂量阈值,也就是说,很小的剂量也可能引发,剂量越大发生概率也越大。
放射线诱发癌症的随机性效应是一种远期效应,一般至少几年后才会发生,例如上文提到的戴利、居里夫人的大女儿大女婿及美国放射学先驱伊丽莎白•弗莱虚曼-阿虚海姆。但我做完CT后才十几天,肿瘤就急剧进展,这与随机性效应的远后性不是相矛盾吗?另外,国际放射防护委员会把放射工作人员的职业剂量限值确定为:(1)连续五年的年平均有效剂量不超过20mSv;(2)任一年内的有效剂量不超过50mSv。虽然该委员会强调个人剂量限值不代表安全剂量,只表示它应该得到遵守,但现实中它还是在一定程度上被赋予了安全剂量的意味。从这一角度看,我三年只做了一次胸部CT平扫,所摄入的辐射量据说最多只有7mSv左右,与50mSv的个人剂量限值相差很多,因此无论从理论上说还是从实际情形看,这都应该是很安全的。
那么,我为什么不顾这些因素,非要把CT检查看作这次肿瘤疯长的元凶?
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些因素都是针对健康人的,不管是放射线致癌的随机性效应还是放射从业人员的个人剂量限值;但我不是健康人,而是一个晚期癌症病人,还是恶性度极高的晚期黑色素瘤病人!在没有外来损害的情况下,我已经活得颤巍巍了,哪里还经得起本性凶猛的放射线,即便剂量不是很大!
具体地说,当我想到是那次CT检查的辐射刺激了癌细胞,造成我肿瘤的急剧进展后,我很快便在目前医疗放射学界的一派歌舞升平中发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这么多年以来,医学影像学、放射医学、核医学和肿瘤学等领域的专业人士在无形中都把医疗辐射的受体设想为健康人,最多把孕妇、哺乳期妇女和幼儿作为特殊人群区别对待,却不知道面对放射性辐射,从其对生命和健康的危害而言,癌症患者才是真正不堪一击的最脆弱的群体(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说的癌症患者仅限身上存在肿瘤,或血液中肿瘤指标超标的实体瘤和白血病患者,不包括已经康复的癌症和白血病患者)。我们的专业人士显然没有意识到,癌症患者只要没有治愈,大部分很快或要不了几年便会失去生命,因而这实际上是一个比孕妇和幼儿还要脆弱得多的特殊群体。我们都知道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这个比喻。为什么一根稻草便能将一头骆驼压垮?因为骆驼本已不堪重负。癌症患者就像一群已经不堪重负的骆驼,他们连一丁点的风吹雨打都经受不起,何况额外遭受凶猛到带有骷髅头标识的电离辐射!健康人做一次CT确实不需要担心,但对于那些生命本就处于危险之中的癌症患者,一次CT的辐射导致肿瘤急剧进展,部分病情较重的患者因此过早地去世,又有什么可以奇怪的呢?!
其实,在复发转移后不久,直到这次复查前,我对放射医学检查(X线和CT等)和核医学检查(PET-CT和SPECT)一直怀着某种程度的戒心。从2012年6月到这次复查前,整整三年时间,我没做过一次CT,更别提全身骨扫描和PET-CT这样的核医学检查项目了。这并非因为哪个人的提醒——没有任何人提醒过我,只是在2012年夏天的某一天,我偶然想到CT是有电离辐射的,而电离辐射可能致癌,于是我觉得自己之前太大意了,癌症病人还是尽量别做CT为好。2012年8月,我还在新浪博客发表了一篇题为《复查的一点窍门》的文章,提醒病友们在做影像检查时尽量用B超和磁共振代替CT,哪怕对于肺部。这样的见识在肿瘤界可谓前所未有,到了今天也很罕见。另外还值得一提的是,我自2011年4月底开始指导潍坊终末期胃癌病友Z的治疗,从那时到2015年5月我的这次复查,长达四年的时间里,我从未让她做CT,只让她做B超和磁共振;即便在最初的一年,我自己还在定期做CT,也从未让Z去做。虽然我在查出癌症前就知道放射线对人没好处,但起初总觉得问题不大,没必要在意。在这样的认知下我一直没让Z去做CT,细想起来也是挺了不起的,我这是在半懵懂半清醒中做了一件大智慧的事。究其原因,我觉得应该是我在潜意识里认为Z的病情太重,经受不起CT的辐射,才没让她去做的吧。以她当时的病情,假如我让她做了CT,哪怕只有一次,恐怕也无力回天了。
照理,对放射线如此警惕的我不应该做这次CT。事实上医生在替我开检查单时原本也没有CT,她根据我此前三年的习惯,针对肺转移仅开了胸腔B超以查看有无胸水。但我自己考虑到那段时间左胸感觉有点异常,想知道左肺有无转移,于是主动要求做个胸部CT平扫。其实知道了左肺转移又如何?还不是继续服差不多的中药!所以我的这一举动属于典型的白痴行为,而对此,我只能用自己的一句人生感悟人有时候脑子会发昏来解释。
可惜我的白痴行为并非只此一例。在我想到CT检查是造成这次癌细胞疯长的元凶后,我的大脑马上对自己和病友的经历做了一番扫描,结果显示我还有过另外两次白痴行为,加速了两例患者的死亡。
第一例是我的远亲M,60多岁,鼻咽癌放疗后皮下转移,脸上短时间内形成一个成人拳头大的凹凸不平的肿瘤,并且很快破溃了,人见人怕。经西医、中医几番治疗无效,整体情况越来越差,钱也花得差不多了,他不想再折腾,就把剩下的时间交给了我,让我用纯中医替他治疗,直到他死去为止。那是2013年上半年的事。
经过我几次调整药方,治疗到一个多月时,他老伴对我说:现在终于感觉到效果了,M的精神和胃口都明显好转,不再整天躺着,爱下楼走动了。我听了也挺高兴,因为之前一年多的时间里我指导着他东奔西跑四处求医,一直是百治不效。
当然,体表巨大恶性肿瘤破溃在中医里属于死症,因而大势并不乐观,但从当时的情况看,我的中药至少能使M在生活质量得到提高的同时延长一段时间生命,这对他和他的家人多少是一种安慰。
然而好景不长。一段时间后,M出现了咳嗽,还有一点胸闷,没有感冒。我判断这应该是肺转移进展到一定程度后出现的症状。鉴于他此前并没有肺转移的诊断,而且最近一年都没有做过肺部检查,我不假思索地让他家人下次去医院配药时把他带上,替他做个胸部CT平扫。
检查过后没多少天,M的病情开始加重。我调整药方,但收效不大,M仍然每况愈下,再也未能恢复到之前相对较好的状态。从他委托我全权治疗到他不治身亡,总共持续了大约半年时间。
由于我接手M的治疗本就属于死马当作活马医的行为,而且他那么严重的情况还能活上半年,效果已经算不错了,因此,周围人都把他的不治身亡看作一件很正常的事,我也没有多想。直到两年后我发现CT检查能刺激癌细胞疯长,才意识到我安排他做的最后那次CT缩短了他的生存期。
第二例是四川绵阳病友B,男,30岁左右,患直肠癌。2014年夏天,在根治手术和放化疗结束大约一年后,他查出肝和肺等处广泛转移。他自己早就摸到腹部的大肿块了,但当时他跟新交的女友在外旅游,为了不留遗憾,拖了一段时间,直到旅游结束才去检查,B超发现肝脏布满了肿瘤,已经没有好地方了,腹腔有少量积液;抽血示黄疸和肝功能受损。同时,他的症状也较严重,乏力,肚子胀得基本睡不着觉。医生告诉他没办法了,不必治了。无奈之下,他请我替他开中药,说希望再活上四个月,替他妈过完生日再走。我知道这种程度的肝转移意味着时日无多,但彼此相识,只能尽力一试。在电话了解病情的过程中,我发现他偶尔有一两声刺激性咳嗽,他自己没在意,但我怀疑他肺部也转移了。为全面了解病情,我不假思索地让他去做个胸部CT平扫确认一下。因他之前查腹部用的是B超,他觉得可能不够清楚,所以在找医生开检查单时,他主动要求加了一个全腹部CT,而且与胸部CT一样都是增强的。检查结果显示,他确实有了肺转移,且肝转移的严重程度与B超发现的相一致。
检查完后,我替他开了四剂内服药。服后他的肺部症状明显好转,但腹胀依旧。服第四剂的当天,有一会儿他突然感到腹胀加重,有一种像是要昏过去的感觉,不得不叫了救护车去医院。他怀疑我开的药方不大对路,我虽觉得自己在治疗肝转移方面经验已很成熟,用药不至于出偏,但他已经发生了不好的情况,我就不敢肯定自己的药方没有问题。于是,我不再替他治疗,推荐他去附近的乐山市找名医刘方柏。我看过刘方柏写的一本书,里面列举了他治疗奇难重症的不少成功案例,其中也有针对肝癌腹水的,我觉得他值得B一试。B上网了解到刘方柏的一些信息后,心里产生了很大的希望。为方便诊治,他干脆到刘方柏所在的乐山市中医院办理了住院。几天后,我问他效果如何,他说吃了刘方柏的第一剂药后曾有一会儿感觉好了些,但很快又不行了。我建议他服麻醉性止痛药,别再忍。之后,他几乎不再跟病友们联系。大约一个月后,我从其他病友那里得知B已去世。可以想见,刘方柏的药对他也完全无效,服第一剂那天曾有一会儿感觉稍好,那纯属偶然,而不是药的作用,否则,后面几天也应该有效才是。
这两个患者的病情都比我严重得多,我接手时第一例已基本卧床,处于终末期了,第二例满肝都是肿瘤,且有了黄疸和少量腹水,也属于终末期了。我自己在2015年复查前,看着像个健康人,但一个胸部CT平扫便使我的病情急转直下,因此,对于这两个患者,一次CT尤其是整个胸腹部的增强CT会有怎样严重的后果,便不言而喻了!想到这里,我感觉额头都要冒汗了,痛心疾首,自责不已!但一切都无法挽回了!
当然,这两个病人即使不做CT也撑不了多久,但如果不做CT,他们至少不会那么快就失去性命。
说到这里,肯定会有很多人提出质疑:癌症病人哪个没做几次CT?他们做的还往往是辐射比平扫大得多的增强CT,而且只要没有治愈,每年至少做一次,有些人甚至还做了融放射性药物与CT两种电离辐射于一体的PET-CT,为什么他们都没事,你三年只做了一次胸部CT平扫就造成肿瘤疯长?你的推断是毫无科学根据的!
其实不要说别人,我自己一开始也提出了这个疑问。不过我很快想到了答案:
(1)那些没事的患者病情相对较轻。CT检查的后果与患者病情的严重程度密切相关。一般说来,在遭受相同剂量电离辐射的情况下,癌细胞恶性程度越低、肿瘤负荷越小,患者受到的危害就越小,反之则受到的危害也越大。像常见的甲状腺癌、乳腺癌、结肠癌等幸运癌的早期,一次CT平扫对癌细胞的刺激通常是患者感觉不到的,而假如是晚期胰腺癌、晚期黑色素瘤这样的癌王,一次CT平扫便足以使肿瘤进展到难以弥补的程度。拿我自己来说,我从2010年4月复发转移到2015年5月复查前,总共做了五次CT(均为平扫),具体时间为:2010-5-9(胸部),2010-9-1(胸部),2011-6-23(胸部),2012-2-27(胸部),2012-5-22(全腹部)。后来回想起来,这几次CT检查后病情都加重了。例如2010年5月做了CT后,6月份查出胆囊转移和肝转移,腹胀腹痛日趋严重,很快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2011年6月下旬做了胸部CT平扫后,8月份出现了骨转移伴疼痛。另外几次CT之后,疼痛症状也出现过反复。不过,由于当时肿瘤较小,我又没被西医碰过,癌细胞增殖的加快没有达到失控的地步,因此没过多久便被我控制住了,我就没有觉得病情的进展有什么异常。临床上癌症患者在做CT检查时,很多时候像我复发后的头几年那样,肿瘤负荷并不算大,放射线对癌细胞的刺激不至于使病情急转直下,于是人们便会觉得做CT检查没事。其实他们并非真的没事,放射线对他们还是造成了肿瘤的进展,只是他们看不到而已。
(2)在做CT之前或之后,癌症病人通常会接受手术或化疗、放疗、靶向、免疫等西医治疗,这些治疗可能有效也可能无效,还可能不但无效反而造成恶化,或者开始有效后来变得无效甚至发生疗效反弹,而肿瘤本身也会或快或慢地进展。这样的患者如果肿瘤出现爆发式进展,其原因就像一笔糊涂账,很难查清楚。人们通常会认为这是西医治疗无效的结果,不会想到还与医疗辐射有关。相比之下,我只用中药且效果一直不错,不存在其他可能导致病情加剧的因素,因此肿瘤进展后很容易查明原因。
(3)有效的治疗可以弥补CT检查导致的肿瘤进展。假设一次全腹部增强CT检查会使某晚期癌症患者身上的肿瘤在三个月内总共增大3立方厘米,但他在做CT之前或之后接受了几次化疗,而这几次化疗能使他的肿瘤在三个月内总共缩小4.5立方厘米,那么他的肿瘤最终仍将缩小1.5立方厘米。在这样有效的治疗之下,人们就看不到CT引起的肿瘤进展!也就是说,并非CT没有造成肿瘤进展,而是有效的治疗掩盖了这种进展。临床上存在基因突变的肺腺癌病人大多每3-6个月便做一次CT,但没有多少人觉得肿瘤的进展明显加快了,其主要原因便在于肺腺癌靶向药效果较好,疗效掩盖了放射线对肿瘤的刺激。所以我有一次对一位肺腺癌患者家属说:如果你们靶向药的效果足够好,那么一次肺部CT平扫的辐射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4)我自己的情况也解释得通。我在2010-2012年间总共做了五次CT,但并没有造成癌症急剧恶化,这一方面是因为当时肿瘤负荷相对较小,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我所服的中药效果不错。在这两种因素的作用下,CT对癌细胞的刺激不是很强,于是被我忽略了。而到了2015年5月,由于我的肿瘤在过去三年里进展了不少,因此一次CT平扫便导致病情完全失控,这才引起了我的注意。
总之,人们可能提出的所有质疑我都想到了,并且都能给予合理的解释,我对自己的判断充满了信心。既然肿瘤的急剧进展是CT的辐射所致,那么我之前的用药就没有问题,不需要也不应该大加修改,而是微调一下便可一直沿用下去。假如我有一点点疑虑,偶尔也认为肿瘤的急剧进展有可能不是因为CT检查这一外来的恶性刺激,而是诸如癌细胞或者中药自身的某些特点引起的,例如癌细胞可能因为一种我们目前还搞不清楚的机制,自己突然加快了裂变,或者像某些中医所说的中药也会耐药,我这种情况可能是中药耐药了,等等,那么我就得大幅度修改药方,或者干脆去找别的中医。然而我并没有。
不过,守方不变并不意味着我认为癌细胞疯长的势头马上会得到遏制,恰恰相反,由于病情持续加重已经一个半月,加上那个鼻咽癌皮下转移亲戚和直肠癌肝转移病友的结局,我判断自己的病情会一直恶化下去,直至不治而亡。虽然我从网上看到,很多医生认为CT检查时摄入的放射线最多一两天便会排干净,但我没法相信。假如放射线马上就会排干净,那么国际放射防护委员会在确定放射工作者的个人剂量限值时为何会有连续五年的年平均有效剂量和任一年内的有效剂量这样的区别?何况我做完CT已经一个半月,肿瘤一直在进展。我推测放射线的排出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短时间内很难排干净。
仿佛是在证实我的推测,我的情况仍在全面恶化:体重继续下降,疼痛和难受的时候越来越多。有一次,替我转方开药的医生去外地开会,隔了两周才见到我(平时我每周一次看她的门诊)。我一走进诊室,她就对我说:你又瘦了一圈。距复查两个月时,我的体重下降了15公斤。至于疼痛,主要是骨痛。腹痛虽然加重了,但贴了一种中药止痛药膏后有所缓解;骨痛则百治不效。不过,即使最严重处的骨痛也仍不是钻心刺骨或持续性的,但一天会发作好多次,伴有烦躁。这种发作没有什么规律,有段时间我连续三四天痛得较少,程度也较轻,以为中药见效了,刚准备总结经验,看看是哪几味药起了作用,不料第二天后背又痛得让我断了所有的幻想,而且连续几天都是如此。
7月下旬时,我对靠中医挽回病势已基本不抱希望,想到了西医的靶向免疫治疗。根据我的认识,同样效果较好的情况下,中药在减轻症状方面可能立竿见影,但在抑制肿瘤方面较为和缓,而西药则无论在减轻症状还是抑制肿瘤方面都较为迅猛。这次CT检查后我的肿瘤急剧进展,中医一直看不到效果,我就觉得或许只有西药才能扭转局面,而当时对晚期黑色素瘤效果最好的就是口服的威罗非尼(Vemurafenib,后来中译名改为维莫非尼)等靶向药和作为注射液的免疫治疗药物K药(PD-1单抗Keytruda)、Y药(伊匹木单抗Yervoy)等新药,它们的问世被称为晚期黑色素瘤治疗上的重大突破。很多人以为像我这样选择纯中医治疗的病人对西医的新药肯定一无所知,所以这些年时不时有患者或患者家属给我发送一些西医新药和新疗法的链接,门诊医生则大多把我看作无知的老农似的,问我为什么放着疗效令人鼓舞的靶向免疫药不用,反而选择不靠谱的中药。其实作为一个学医之人,我大概是国内最早了解国际上黑色素瘤治疗新进展的少数人之一。那些年上网管制还较宽松,学历不是很高的人想上境外网站可能有点困难,但像我这个知识层次的人只要稍微用点技巧,访问任何境外网站都畅通无阻,所以我时不时查阅wikipedia,并去西方几个癌症病人交流论坛潜水,记下了一些诸如靶向免疫治疗、质子重离子治疗的优势和成功病例等信息。在国内还没几个癌症病人知道质子重离子治疗的时候,我已能随口说出质子与重离子治疗孰优孰劣,它们的优势和适用范围,全球和国内第一台质子治疗设备分别装在哪里等等。我曾跟人开玩笑说,我与国内黑色素瘤权威郭军不但同龄,还是同学:在同一时间学习国际上黑色素瘤治疗的新进展,只不过他看的是临床报道,我看的是患者在网上的反馈。总之,选择纯中医治疗不代表我不了解西医西药知识,只不过后来上网管制加强,我虽然仍能通过某些手段访问部分国外网站,但使用体验较差,更重要的是在仔细了解后,我觉得目前西医所有的新药和新的治疗手段都不如中药实在,因此我不再关注。
那个时候,靶向免疫药的价格十分昂贵,例如口服药威罗非尼一个月的花费至少要八万多人民币。考虑到我的肿瘤应该增大增多了不少,PD-1免疫治疗效果估计有限,加上其价格超贵,注射液使用又不便,我打算如果选择靶向免疫治疗的话,就只用口服药威罗非尼,盲试,一个月为期,有效的话一个月后回归纯中药治疗,无效的话我肯定很快就没命了,也就什么都不用操心了。有医生提醒我这么做是胡来,我说我是信命的人,这样的选择也是基于个人的基本情况并经过慎重考虑了的,如果我命不该绝,就会取得效果;如果命中注定我逃不过此劫,那么就算选择最佳方案也没用。
除了价格昂贵,这些药当时还要去境外购买,例如香港,国内还买不到。于是我申请了港澳通行证以备不时之需。当工作人员告诉我十几个工作日后才能取件时,我的第一感觉是这个时间太遥远了,很可能通行证还没拿到,我已经没有力气出门了。因为症状仍在加重,现在骨痛发作时除了伴有烦躁,有时还有一种崩溃感——这使我想起了那位直肠癌肝转移的四川病友B。他服我的第四剂中药那天,腹胀突然加重,有一种要昏过去的感觉,不得不叫救护车去了医院。他怀疑是我的药开得不对路才会这样,我自己也不敢说他的怀疑没有道理。然而,当一年后我因为骨转移痛得要崩溃时,我突然意识到,B当时腹胀的加重与我的药并无关系,而是增强CT的辐射刺激癌细胞疯长所致,像是要昏过去的感觉不就是严重的崩溃感吗?他的病情比我重,摄入的放射线也比我多,所以他的崩溃感也比我强。
所幸我拿到港澳通行证时,虽然整体情况仍然很糟,但还能自理。
不过我并没有去香港买药,甚至都没怎么考虑此事。我的理由除了靶向药价格昂贵、副作用大、疗效不确定、即使有效也会很快耐药外,主要还在于它可能改变原来的的死亡方式。那时我已观察到一个奇怪的现象:用靶向药和免疫治疗药的患者即使有效,也容易发生突然死亡,尤其是在后期。有的患者刚刚看着还不错,能吃能走,几天后突然就死了。这与服中药有效的患者的情况恰恰相反,后者往往是一步步缓慢地走向死亡,像是油尽灯枯的一个过程,很少有突然死去的。相信大部分癌症病人喜欢前一种死法,只有需要更多时间完成某些事情或特别留恋生命的人才会喜欢后一种。杭州名医陈友芝医案中有一个严重的晚期肺癌多发骨转移患者,确诊时其单位即将福利分房,如果他能活上一年,就可以分到一套房子留给儿子;如果活不到一年,单位分房就没他的份。为了儿子,他在中医的帮助下苦苦支撑一年,终于在死前拿到了房子,放心地闭了眼。重庆儿童文学作家杜虹则属于特别留恋人世的类型。在2014年查出胰腺癌后,无论痛得多么厉害,为了活着,她都咬牙忍受;她还决定将她的遗体交给美国一家科研机构冷冻保存,等50年后再解冻以争取复活,到那时也许胰腺癌已经被攻克了。不过这家科研机构认为她的躯体不适合冷冻,建议只保存头颅,费用为12万美元,到2065年解冻,届时看看她的记忆能否复活。2015年5月底,60岁的杜虹去世,家人真的替她完成了此事。
从意愿而言,我也希望前一种死法,尤其是因为我颈椎和胸椎的骨痛最为严重,有可能因病理性骨折而全身瘫痪,这是我不能忍受的。然而,由于我的病情是突然恶化的,很多事情来不及完成,因此我又不能突然死去。例如,作为一个水平还算不错的中医,我的生命不只属于我个人,假如我突然撒手而去,那么像上文提到的病友Z这样在我这里治得不错的患者就会面临危险(补记:2022年5月我病危住院后不久,终末期胃癌已带瘤生存11年的Z也确实因为我顾不上她而不幸离世,年仅34岁)。为了那些需要我的人,我应该尽量多活一段时间,在替他们继续治疗的同时,争取把他们在我死后的治疗事宜安排好,而这需要很多时间和精力。为了这一目标,可能缓解病情但也容易缩短生存期、甚至可能造成突然死亡的靶向免疫治疗就不在我的考虑范围,而我当时的中药虽然看着无效,但至少不会造成突然死亡。
到8月份时,受一个儿科偏方的启发,我加服了一味刺激胃口的药。由于此药比较另类,在此就不透露了。几天后,我发现自己又有了一点饥饿感,但这种饥饿感并非正常的那种,而是带着少许不舒服,需要马上进食胃里才会好受一些。不过,对于一个已经麻木的胃来说,能够产生这样一种饥饿感也是好事。
到8月下旬时,我发现进行性消瘦的势头明显减弱了。
不过我依旧无法得出病情开始好转的结论,因为疼痛和难受更加严重了。医生替我开了解热镇痛药西乐葆,这属于癌症的第一阶梯止痛药。考虑到自己有过药物性肾损伤,加上西乐葆曾遭倪海厦点名批判(说它本来不叫西乐葆,因严重心血管不良反应被FDA取缔后,换成西乐葆的名字重新上市),我暂时忍着没服。与此同时,我还出现了一个患癌以来从未有过的症状:经常出虚汗,开着空调躺在床上也会冒汗,在室外就更严重了。还好那年夏天气温不高,否则光是虚汗就能把我打垮。
9月份时,整体情况继续恶化,出现了又一个以前从未有过的症状:癌性低热。这是我第一次出现癌性发热。
10月至11月,疼痛和难受继续加重,我不得不服用西乐葆。刚开始的三四天,疼痛有一定缓解,但之后就无效了。于是我吃吃停停,先后服了大约一个月的量,感觉疼痛减轻的日子却最多只有一周。医生说第一阶梯止痛药对我无效,建议升级到第三阶梯,也就是吗啡、羟考酮等麻醉性镇痛药。我起初不愿考虑,因为无论是美施康定(吗啡缓释片)、奥施康定(羟考酮缓释片)还是多瑞吉(芬太尼透皮贴剂),都会让人昏昏沉沉,那我还怎么干活?但后来实在有些挺不住了,我就想:豁出去了,吃!于是之后总共有三次,当医生建议我服麻醉药时,我都表示同意。不过,每次都有客观因素让我没有配成药:第一次是医生没带麻醉药品专用处方纸,她对我说:你要是熬得住,就等下周我带了麻方来时再开;要是熬不住,那我现在就去拿。我说那还是等下周再配吧。第二次是我想从最低剂量开始,10毫克的美施康定或5毫克的奥施康定,但那家医院没货。第三次是因为什么而没配成我已记不清了。如果用弗洛伊德的理论进行分析,便可知道我的潜意识一直在抗拒麻醉性止痛药。
不过癌痛面前无坚强,假如癌细胞完全不受控制,那么这种抗拒不管有多顽强,都无法维持长久。换句话说,我的中药看似无效,其实还是起作用了。假如中药完全无效,我肯定早就卧床不起,并早早地吃上了麻醉性止痛药!我庆幸自己的坚持。那段时间,不只一个病友/网友提醒我:你的肿瘤已经持续进展好几个月了,你该转变治疗方向了!有人建议我去住院,有人建议我找中医治癌正规军中数一数二的人物林洪生、刘嘉湘等人,也有人建议我找民间中医谁谁谁、谁谁谁……他们认为,CT刺激癌细胞疯长毕竟只是我的推测,没有得到科学的证实,我不能死守着一个没有科学根据的推测……其实我自己也在头脑里认真思考过几回,检查自己会不会看走眼,结果每次我都肯定自己判断无误,并由此决定继续效不更方。
效不更方并不意味着用药一成不变,实际上我的药方一直都有少量调整,只是大的方面始终没变。概括地说,我当时的用药无非是复查前用药的加强版,即只是加大了复查前用药的药力,并增加了几味扶正(之前我几乎从不扶正)与开胃消食药而已。我觉得既然肿瘤的急剧进展是CT的恶性刺激所致,治疗的原则就无需改变,也就不宜对药方大动干戈。我相信两点:第一,中药吃总比不吃好。第二,吃我自己开的药总比找其他中医好。
不过,这样的自信并不代表我认为病情有望好转,恰恰相反,8月份的时候我已认定大势已去,下个月是否熬得过都很难说,再活三个月更是不可能的事,所以,我把冬天的衣服被子都清理掉了。后来,随着疼痛的加重和癌性发热的出现,过着这个月不知道下个月的感觉就更强烈了。
在这种情形下,我又展现出其他晚期癌症患者少有的一点:既没有住院寻找希望,也没有东奔西走寻医问药,而是抓紧时间干活,希望把想做的事情多完成一些。我觉得人最后反正都是要死的,谁都无法避免,这是这个世界唯一的、终极的公平,那为何还要徒劳地挣扎?即便垂死挣扎可以延长一年半载的生命,但面对无限的时空,这一丁点延长又有什么意义?记得当时曾经有人问我:你是怎么克服恐惧和绝望心理的?我回答说:我没有时间恐惧和绝望,做事都忙不过来。在我患癌近30年的其他时间里,我也好几次碰到过这样的提问,每次我都是类似的回答。每一个癌症患者都存在对死亡和遭受病痛折磨的恐惧心理,对我来说,忙于事业最能克服(至少是忘却)这种恐惧。
当然,宗教信仰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据我观察,大部分癌症患者把佛教或基督教当作自己的精神支柱,以此抵御对死亡的恐惧。作为一名资深(近30年)佛教徒,我的信仰也使我能比较淡然地面对死亡。远在三四十年前的大学时代,我就明显地表现出宗教信徒的潜质,对那些无神论者感到无法理解,并且觉得自己有朝一日总会成为基督徒。虽然后来阴错阳差被人引入佛门,但我觉得佛教与基督教在本质上没有多少差别。一般人都以为我之所以信仰宗教是因为患了癌症,只有我自己心里明白,这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事,它植根于我对宇宙和人生的认识,与癌症关系不大。这个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过程使我的信仰比其他癌症患者坚定而清醒得多。
就这样,凭着对自己判断的信心,凭着事业和信仰这两大支柱,我在面对死亡的威胁时得以保持冷静,沉着应对。如果换成别人,看到肿瘤一天天进展,早就乱了方寸,不是认命放弃,就是乱治一气,或者把自己交给医院,而当时医院对这种情况并没有什么好办法。不论选择这三者之中的哪一种,最后都难逃短期内死亡的结局。
不过作为一个凡人,焦虑是我未能克服的。由于各种难受的症状,我的工作效率很差,加上病情持续加重,我总感觉连计划的最低量都完不成,于是难免焦虑。例如我当时一个很大的工程是替病友Z写一份《今后用药指南》,让她和家人在我死后可以据此选择西医治疗手段和中医用药。这是一项十分复杂而困难的工程。Z当时病情稳定,基本没有症状,但她毕竟是带瘤生存,一旦没有了我的指导和治疗,要不了多久病情便会加重,对此我首先要想到病情加重的各种可能,然后确定相应的治疗方案和中医用药,让毫无中西医基础的Z及其家人可以按图索骥。这样假设性地治疗一个病人比现场治疗一批危重病人还要困难,我折腾了两个月左右才搞出一个初稿,间隔一两个月后又搞出一个修改稿,而结果仍然粗糙,于是我禁不住担忧。
计划中的事情还忙不过来,不料又多了新的事情。9月下旬,一个远亲打来电话,说她孙女H今年才19岁,三年前上学期间得了卵巢癌,切除了右侧卵巢,并就此辍学;今年不幸复发,且发现时已是晚期,于6月份做了肿瘤细胞减灭术,切除全子宫、左侧附件、大网膜、阑尾和盆腔肿块,术后化疗,但并无效果,出现了大量腹水,医生告知家属没有希望了;家人不忍放弃,想起我20来年前也是晚期癌症,靠中医一直活到现在,就来找我帮忙。他们不知道我此时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根据我几个月来的病情进展速度,我觉得我肯定会走在H之前,不适合替她开药,而且H是西医积极治疗却归于失败的病例,中医很难取得效果。但H的遭遇实在令人同情,我没法置之不理。碰巧H的一个亲戚是当地人民医院的中医内科专家,三年前H做了根治手术后就是找他开的中药,于是我决定让他给H治疗,我则提供一些指导性意见。为此,我先替H开了几次药投石问路,然后就她今后的诊治写了一份详细的看法和建议,给她的中医亲戚作参考。不过,由于H的病情一直控制不住,后来我仍然经常与她沟通。
就这样,我在病情显然已处于终末期的情况下依然忙碌着,而这似乎在为我多年前就有的一种预感提供着最后的实证:当时我就对人说,我这辈子应该是个劳碌命,这是我无法摆脱的宿命。
然而,上天似乎不想我过早地结束劳碌。12月下旬时,我突然发现七个月来一直在我身上作乱的癌细胞似乎平静下来了:体重稳定,癌性发热消失;疼痛虽然仍会发作,但不再伴有烦躁和崩溃感。到1月上旬,病情仍未反复,我就知道肿瘤爆发式进展的态势被遏制住了,回到了原来那种较为缓慢的速度。不过,癌细胞七个月的疯狂所造成的肿瘤进展是无法逆转的了,因而我的身体不可能再回到这次复查前的状态。这就像一个遭受强敌入侵的国家,虽然经过激烈的抗战赶走了侵略者,但国土已变得满目疮痍。